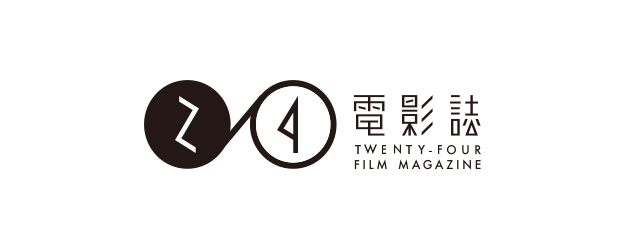關於畫外音(off-screen voice):書寫與衝突
從我的觀影心得中,我特別想把塔可夫斯基電影中的畫外音和《自由之心》做一份比較。
在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中,時常一個人物(先代稱為A)的臉龐來到了鏡頭前,他對著鏡頭微笑,此時鏡頭的涵義,可能是另一個人的主觀視野,或只是一個攝影機的運動捕捉到他對於後方事物的反應。此時,出現了畫外的聲響,這個聲響多半是另一個人(代稱為B)的高呼,這個高呼或許是反應了某個危機,或是某個突發事件--總之,他一定會和A的命運有關係,直接導致A的動作,或許是奔跑,或許是死亡。
這段畫外音,勢必不是和A回頭的時間點相同的,因為如果是「A回頭」這個時間點的高呼,會引起A的注意,A也不會露出那麼和睦,甚至是憨愚的表情--所以,畫外音的時間是晚於人物表現的。這使得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多了一份詩意:鏡頭前的人物和景緻表現地靜謐、和諧,猶如風景或肖像畫,但是宿命又會將人物帶往不同的地方:畫外音是「宿命」,被擺置到了「現在」的景框中。
無論是《安德烈‧盧布列夫》(Andrei Rublev, 1966)中韃靼人殘忍的屠城,還是《鏡子》(Mirror, 1975)中孩子窺視等待父親、孤單的母親,還是《索拉力星》(Solaris, 1972)中,與亡妻幻影相見的情感,都被這樣的宿命美感給囊括其中。
一般文本的書寫在一個時間內,大多只能完成一次的描寫;塔可夫斯基的電影卻能藉由畫面和畫外音重疊,達成宿命和現在的二重奏。
在自由之心中,Tibeats唱的《run nigger run》與眾黑奴伐木的場景重疊,也如同塔可夫斯基的電影,有不同時間的重疊,但是在哲學性上,卻輸塔可夫斯基的電影一截,這是因為兩者強調的地方不同,塔可夫斯基的畫外音是一種哲學,而自由之心的畫外音則是現實性的加強。
在自由之心卻另有一個地方與上述不同。其中,當Mr. Ford在台上佈道時,同時在畫外傳來哭聲,這是台下Eliza的哭聲,這位不幸的女黑奴,他的兒女被賣到其他莊園,因此她鎮日痛哭。
在上一個場景,她與主角Solomon爭辯結束後,她告知了Solomon黑奴終將面對的不幸命運,並且獲得了一個可以嚎啕大哭的機會,她的哭嚎於是從這個場景來到了下個場景,成為這個粉飾太平的世界中,「另一個世界」的聲音。而到了下一個場景,Solomon和Tibeats爭打,導致了Solomon更不幸的人生經歷,也正面回應了、驗證了Eliza的論點,使Solomon被迫脫離Mr. Ford相對安全的莊園,而進入到恐怖的、卻也是真實的Edwin Epps莊園。
於是,畫外音達成了另一個功效:畫外,既可以代表宿命、代表動作的強化,也可以代表另一個世界永遠不能由另一個世界所捕捉,因而與景框內的世界衝突。而這也與《自由之心》強調的角色歷程相符:進入到陌生的場域,面對逐漸滲透的殘酷「真實」。
凝視畫外的世界:與「真實」的會晤
「畫外」是電影中的一個重點。Solomon剛開始被帶到了莊園成為奴隸,整部電影中,他的經歷也成為美國黑暗歷史中,奴隸世界的展開。他的展開世界中,他已置身處之的是畫內,而仍未知、逐漸浮現的是畫外。
在這個陌生的世界中,陌生的事件成為凝視的焦點,也因此這部電影中,有許多Solomon凝視的正拍鏡頭,像是片頭他凝視著前方的主人指揮如何伐木、在森林中遇見印地安人等等,就連最後回家時,面對十二年未見的家人,也多了一份凝視的陌生感,被凝視的人或物也透過靜觀而多了一種省視的意味
暴力也是這個新世界的一種陌生,來到奴隸世界的Solomon,在試著逃出Edwin Epps恐怖的莊園時,衝進了吊死黑人的場景之中,他和黑人們面面相對,離別時瞥了他們一眼;這是原先世界中的人物,瞥見了另一個世界的真實,而在這部電影中,這兩個世界又是多麼的近。夜晚中,主人來省察想要逃跑的Solomon,和一位走在懸樑上,夾在主人和主人夫人之間無所適從的女奴Patsy,這些人,都離那個吊死人的畫外世界非常近。
最後,當鞭打Patsy的殘忍畫面,正對著鏡頭長達幾分鐘時,黑人生活的在畫外展開的殘酷環境,被正面、直接地放在景框之中,畫外的世界終於完全進入畫內,Solomon也幾近完成了畫外世界的接觸;因此,在敘述時間上,這個事件也接近了《自由之心》悲慘故事的尾聲。
(文/黃英嘉)